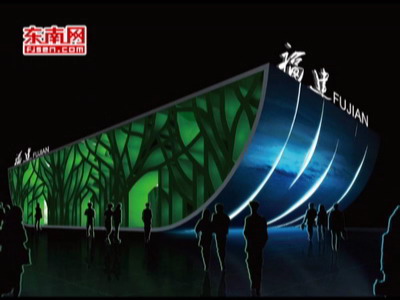論者還注意到商會與政府間利益合作的關系。張志東更提出“超法的利益合作關系”以修正虞和平的觀點。陳忠平認為應將商會當成一種“具有自身社會經濟利益與政治策略、并為此與不同政權進行合作或抗爭的地方商人精英組織”。由于利益的關系,所以有時政府對商會采取的手段便傾向“懷柔”,甚至有意推崇商會的地位。
■與行會的關系:行會的結合體還是行會的替代品
商會與會館、公所(或所謂“行會”)的關系也是一個爭論較多的問題。最初,一些論者認為新興的商會屬于開放性、發展性的工商組織,而以會館、公所為主的“行會”則屬于封閉性、停滯性的社會組織,對經濟發展有阻礙。但是各地的商會史料卻反映出這兩種商人團體并不是水火不相容,反而前者以后者為基礎,多數地方商會還通過維護會館、公所的制度來達到其管理與動員商人的目標。于是,一些學者努力做進一步的探究。
徐鼎新、虞和平、王日根等人均認為商會之所以能容納“行會”,是因為“行會”具有一些“近代化”或者“進步”的特點,因而才能和“現代的”或者旨在“發展資本主義”的商會兼容。但當“行會”加入商會時,卻給商會帶來了“傳統性”。因此,虞和平反對“一方的興起必然以另一方的衰落為前提”的看法,范金民亦認為二者之間“是發展與進一步發展的關系”。
以上論述的目的在于解釋為什么現代性的商會會“收容”傳統的“行會”。那么,如果假設傳統的“行會”未加入,商會自身是否亦具有一些“傳統性”或“落后性”呢? 黃福才、李永樂認為清末中國的商會雖然是新生事物,但仍具有不同程度的“封建性和買辦性”,因而它與“行會”有共存的基礎。王翔則認為商會“本質上只是諸種行會的結合體而已”。如此說成立,那么商會與會館公所自然沒有什么根本的區別了。
范金民提出:商會沒有替代會館公所的作用,而且必須通過會館公所才能充分發揮作用。邱澎生亦發現商會與會館公所間經常形成一種“分工網絡”。他們似乎都強調了二者相互依賴、相互滲透的關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