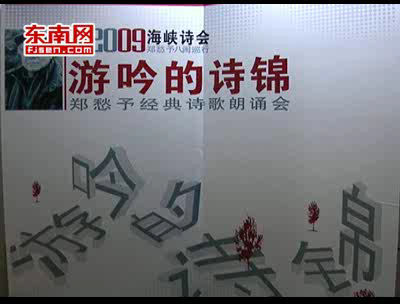大家都知道奧巴馬的當選受新媒體的助力有多大,或許我們可以把奧巴馬政府推動的潮流命名為“網絡外交”(network diplomacy),其涵義可以從兩方面去理解:首先,傳統上由外交官僚體系主導的國際政治正在發生變化,因為全球化與信息科技革命的影響,更多“非政府行動者”通過各種方式介入外交決策過程,影響民意,分享國際政治權力,民間機構的重要性并不亞于政府部門。可以說,當今的國際關系網絡是以做決策的政府為中心,在這中心以外則包含了各種錯綜復雜的關系形態,比如:1.民眾與媒體;2.民眾與政府;3.政府與媒體;4.政府與非政府組織;5.政府與政府。而外交人員的行為角色越來越像是國家(政府)與這個政策網絡間的“跨界聯系人”,必須整合所有可用的公私部門資源,建立一個涵蓋政府有關部門、非政府組織、企業界、學術團體等的全球網絡,形成某種“意志的結盟”,從而才能使外交政策的效應達到最大化。
其次,在具體的操作層面上,“網絡外交”也指外交人員充分應用新的互動工具,發揮信息的利器作用,并推動對己方之外交政策有利的網絡社群的形成。網絡力量的展現一在于去中心化,二在于多樣化。較為傳統的網絡工具早已被用來進行國際宣傳或國際社會動員,比如,建立專門的網站提供信息服務,使用電子郵件游說目標對象等,然而這種“自力更生”式的宣傳模式一方面覆蓋面有限,另一方面亦欠缺Web 2.0時代所看重的傳者與受眾間的互動性。所以,新時代的網絡外交,須充分運用網絡科技所架構的全球性“連結”,以及因連結而形成的“虛擬國際社群網絡”,主動將信息經由網絡傳遞到最大范圍的虛擬國際社會。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網絡科技對于外交的影響不僅是加快信息傳播速度、降低信息傳播成本那么簡單,它也改變了外交的內容。首先是信息來源擴大了:過去的外交內容主要由外交人員為主的相關精英分子所提供,但網絡科技改變了這種信息來源的管道,外交工作的對象不僅變得更多元(包括非政府組織、學術界、國際媒體、基金會等),其信息匯集的通路也由過去的正式管道(如情報、外交單位、特定專家)擴及更廣泛的其他媒體、網站甚至一般民眾。其次,過去以政治、軍事為主導內容的外交運作現在必須面對更多樣化的議題,包括人權、跨國犯罪、恐怖主義、環境等,都有賴于外交手段的介入,外交人員不能再完全獨占外交議題走向的主導權,反而必須花費更多時間與精力于“非高度政治性”的議題。
在網絡時代,不僅外交人員的情報信息中介角色及為國際議題設定框架的能力被減弱,其外交專業地位也受到挑戰。在此情勢下,外交官可不“E化”乎?這方面,美國大使館給世界外交官們上了很好的一課。
- 2009-11-12“甲流”正在加速經濟生活向網絡“遷徙”
- 2009-11-11網絡表達應遵循基本的傳播規范
- 2009-11-07整治網絡低俗之風不能僅靠曝光譴責
- 2009-11-05網絡刪帖屏蔽了百姓呼聲
- 2009-11-05網絡刪帖行為需要規范
- 2009-11-04網絡染上公關病拷問立法缺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