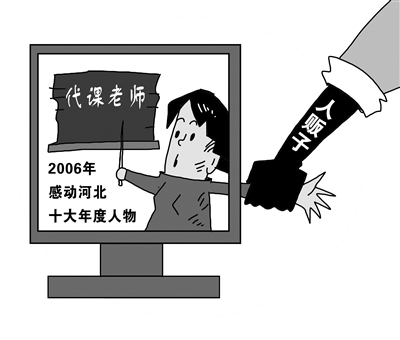
7月28日,兩年前發表的一篇報道《最美鄉村教師候選人郜艷敏:被拐女成為山村女教師》被網友翻出,引發巨大爭議。1994年,18歲的河南打工妹郜艷敏被拐賣到了太行山深處的曲陽縣靈山鎮下岸村,受盡磨難后,她成為該山村小學唯一的女教師。2006年郜艷敏被評為“2006年感動河北十大年度人物”,其經歷還被拍成了電影。公安部打拐辦主任陳士渠發微博表示,“人販子必須嚴懲,買主也必須追究刑事責任。對受害人應當救助,不能縱容拐賣、同情買主。已部署當地警方調查。”
讓受害者真正得到拯救
盛翔
郜艷敏被拐賣事發于1994年,距今已21年了。在這21年里,她經歷的那些不幸遭遇,不僅是她本人痛苦不堪的回憶,也是當地人眾所周知的事實,更是被媒體廣泛報道過的舊聞。2007年1月,郜艷敏手捧“2006年感動河北十大年度人物”獎杯孤零零地回到村里。2009年,她的故事被改編成了電影《嫁給大山的女人》。詭異的是,拐賣她的人至今仍然逍遙法外,沒有任何人對施加給她的傷害承擔過任何法律責任。
倘若不是“萬能的網友”重新翻出了她的故事,并且引起了公安部打拐辦主任的關注,那么,這個被拐賣到河北農村的河南姑娘,注定將會這樣度過她的一生,好像她原本就是一個入鄉支教并且長期留了下來的女教師。讓人費解的是,她都已經“感動河北”了,她的故事都被拍成電影了,如此“事先張揚”的一樁拐賣案,為何一直未曾引起當地公安機關的注意?是21年都破不了案,還是從未試圖去破這個案?又或者,被拐賣的郜艷敏根本不需要救助,而拐賣她的人也根本無需被追究刑責?
“感動河北”的拐賣案竟然也會爛尾21年之久,如此匪夷所思的故事情節,非失職瀆職所無法形容也。被拐女成了受人尊敬的鄉村女教師,從自強與助人的層面,郜艷敏的故事的確足以“感動河北”;可問題是,評選機構在分享和唱誦她帶來的“正能量”之余,有沒有真正關注過她同時也是一樁拐賣案的受害者,是需要被救助的對象?這樣的典型案件、典型人物,怎么就沒有人來重點查辦呢?
當郜艷敏捧著獎杯孤零零地回到村里,當改編電影的人“消費”完了她的好故事,當聞訊趕來采訪的記者被當地政府以維護形象的名義阻撓,冷漠與麻木自始至終圍繞,正義與溫暖遲遲沒能到達。在那么多被拐賣的婦女中,郜艷敏能夠因為當了女教師而受人關注,本來已經算非常幸運了;可即便如此,她卻并未因此改變人生的軌跡,與其他至今無人知曉的被拐賣者別無兩樣,承受了同樣屈辱的命運。
這些年來,打拐一直是備受關注的社會熱門話題,公安部門為此部署了多輪專項行動;但是,如果“感動河北”的拐賣案也會爛尾,人們就不得不懷疑:究竟有多少受害者真正得到拯救,又能有多少犯罪分子真正得到懲處?
每一樁熱聞都不應該爛尾,每一起案件都應該有回復。這絕不只是郜艷敏一個人的悲劇,這也絕不只是郜艷敏一個人的渴求。
悲哀的忘卻與糾結的救贖
然玉
所謂“感人故事”的最開始,竟是一樁絕望的悲劇。郜艷敏蒙難、抗爭之初,未能得到一絲有力的支援;其順服、認命之后,反倒成為催淚煽情的“偉大人物”。在歲月的沖刷下,原本的是非對錯,原本的罪惡與屈辱,似乎正一并變得含糊——若不是有心人舊事重提,又有誰還會記起,這位感人的鄉村女教師,其實是一起犯罪的受害者。厘清此一前提,再來審視她的身份變換和人生轉承,想必更多了許多復雜況味吧。
因為時間的演化效應,郜艷敏一事已經變得無比棘手。作為被拐者的郜艷敏,早已是“買主”的妻子,有了共同的孩子,安處于穩定的家庭結構與情感紐帶之中。從之前的不甘、抵抗,到如今的淡然、接受。郜艷敏的處境和心境,確乎發生了極大轉變。那么,又有誰能說清,怎樣一種未來,才是對郜艷敏最好的結果?公眾所期待實現的“正義”,卻很可能會給郜艷敏造成又一次的傷害。而這,儼然構成一個兩難困境。
針對此事,公安部打拐辦主任表示,人販子必須嚴懲,買主也必須追究刑事責任。這一番表態,既合乎法律表述,也契合民間呼吁,當然值得力挺。然而事態的復雜性在于,郜艷敏與作為“買主”的丈夫,業已具備了一定的感情基礎,且有了相當一部分共同利益。倘若此時追究后者的刑責,很可能在客觀上讓前者的生活更糟。
當然了,上述種種糾結,更多只是情感或功利層面的盤算,不足以左右案件的最終走向。眾所周知,拐賣婦女乃是刑事犯罪,屬于公訴案件的范疇,這意味著受害者的個人意愿,很多時候并不是決定性的……透過此案,我們實則最應意識到,拐賣犯罪的特殊性之所在:倘若無法在短時間內,將被拐女性解救出來,便會造成種種不可逆的后果。長時間的共同生活,以及由此衍生的“后果”,極可能模糊掉施害者與受害者本來清晰的界定。
郜艷敏的曲折人生,讓我們不得不去思考,怎樣才是對被拐女性的最好救贖?就此而言,最理想的狀態,當然是及時將之解救。但,對于那些延續太久、已產生“既成事實”的拐賣事件,又該如何對待呢?之于此,整個社會顯然還沒有成熟的應對方案。而大致可以預見的是,恰是由于缺乏完善、系統化且有針對性的救助體系兜底,我們便很難對拐賣案中的“施害者”充分追責。于是乎,才會有無奈的忘卻與寬恕,甚至于粗鄙、廉價的煽情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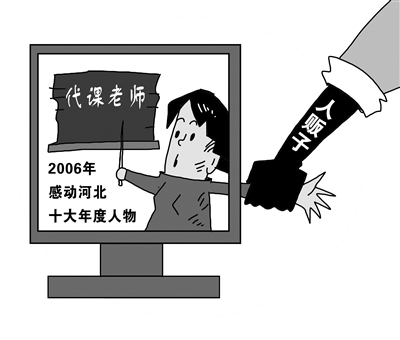
16b14d8e-d040-4dd1-a904-212ae8fad2bf.jpg)
e6f1fe69-bd2b-44af-b1a8-eb4514b48b17.jpg)

ddc0884b-0d56-40c0-b547-f663af484a29.jpg)






